
李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与邻接权教席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尤其偏重基础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专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论文《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化”》《“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为模型》。暇以诗文创作为娱,有志于“以美文抒法理”,曾发表《法题别裁》等系列知识产权随笔。
版权闲话之二:创造观的历史性与人文意义
“作品是人创造出来的”,在今天看来不容质疑。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希腊人的词汇中,没有与“创造”和“创造者”相当的词,他们描绘艺术活动的词相当于“制造(make)”。在柏拉图看来,即使是“制造者”的头衔也不适用于艺术家。《理想国》借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表达了这个观点。对话者假设了一种情况:神造出自然之床(床的理念),木匠做出现实之床,画家画出艺术之床。他们认同,神和工匠都是制造者,但画家却不能被称为制造者,他只是个摹仿者。因为柏拉图认为艺术品是摹仿之摹仿(现实之床摹仿理念之床,艺术之床摹仿现实之床),离真实最远,所以对艺术的地位是贬斥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体系也是以摹仿论为基础,他在《诗学》中认为,一切艺术总的说来都是摹仿。一旦艺术的目标被认为是追求真实或完美,彰显作者的个性无疑会妨碍这种追求。因此摹仿论排斥独创。“诗人应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讲话,因为这不是摹仿者的作为。”
这些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观点,需要放在历史的视野中去理解。对作品的解释,也是人的自我理解。就像个人认识自我比认识外界更难一样,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从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古希腊哲学家首先从作品与自然的关系上理解作品的生成,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此时,主体的自由意志尚未被充分揭示,人类还像初生的婴儿一般,只知向外张望。此时的艺术,还只是被视为发现,而非发明。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
到了中世纪,“创造”一词仅与上帝相连。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意识逐渐提升。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取最初的知识。而皮科在其演说《论人的尊严》中则指出,上帝对亚当说:“我把你造成一个既不是天上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人与其他生命的区别在于,他不是被规定的,可以自由地选择堕落为野兽或再生为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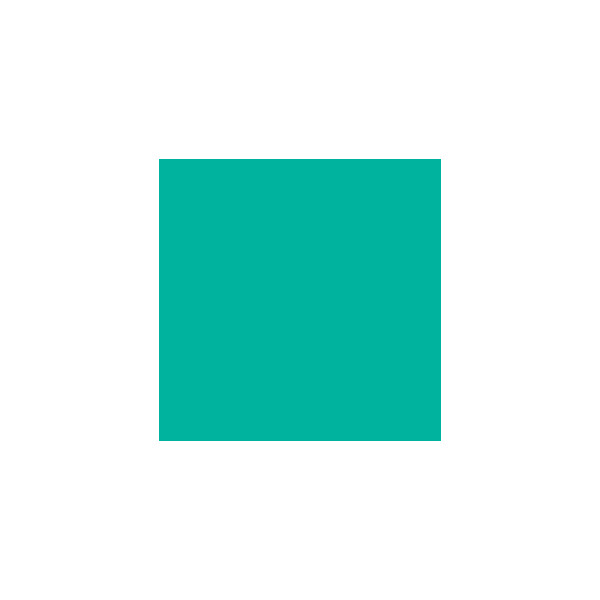
不过,自由意志的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有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开始抛弃摹仿说,从作者“自我表达”的角度解释作品,“然而,他们还没有大胆到启用‘创造者’一词的地步”。直到17世纪,波兰诗人沙比斯基才开始用创造者称呼诗人,但依然认为诗歌以外的其他艺术只是模仿、复制,谈不上创作。 随着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自由意志是人的特质”这一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相应地,作品也更多地被视为主体自由的表达,而非对自然的模仿。这个过程正如谢林对艺术史的总结:古希腊艺术更强调必然性,近代艺术则着重发挥了个体性和自由的理念。
由此可见,“人是作品的创造者”这样一个在当今被视为常识的陈述,是伴随着人类漫长的自我省思的过程才得以确立的观念。只有回望历史才能看清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创造作品”常常被不假思索地作为前提,隐含于“机器人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谁”的提问中。因为在“人可以创造作品”变成常识之后,我们判断“创造”的标准主要集中于“表达是否有多样性的可能”。人工智能产生事先不可预知的、非唯一的结果,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这是否就等于“创造”呢?如果我们追溯“人是创造者”的证立前提——“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体”,答案显然不那么确定。创造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主体可以做出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更在于这是出自主体的自由,人意欲表达自身。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一棵脆弱的苇草。在体能甚至智能的某些方面超越人类的动物早已存在,人为万物灵长的优越,不在能力,而在自由意志。一个动物的强韧不是它自己选择强韧,而一个人的软弱是出自自我选择。一个软弱的人并不会在一头强韧的动物面前输掉自己的人性,他的人性依据不是来自软弱,而是他永远拥有选择强韧的可能性。同样,人工智能产生符号形式的行为是不是创造,不能仅仅依据该符号形式是多么的不可预料、多么赏心悦目。“创造”概念的历史性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它以意志自由为中介,构成近代哲学中的人性基础。美学和法学都把作品界定为“表达”,这个词已经暗示了主体的能动性。没有驱动表达的自由意志,至少在哲学意义上,生成符号形式的行为不是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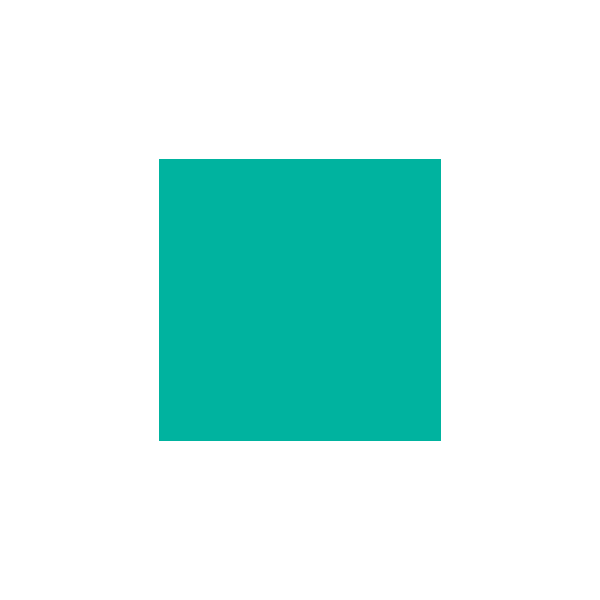
无疑,法律有其独立的功能,对于同一个概念,可以建构不同于哲学的定义,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哲学。至少对于一个极具人文意义的概念,法学不能轻佻。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符号表达在财产价值上与作品相当,也需要法律分配利益,这倒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创造”原本就是权属依据之一种,引入其他因素作为分配依据并没有什么障碍,现行法已经把资本、效率等其他因素也作为权属分配依据。
人类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敢宣称“和神一样,我们也是创造者”。“人是创造者”的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描述,更是价值选择。人选择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而存在,也选择把自身精神活动的产物视为自我的表达,把自我作为作品的第一源头。人是否放弃作为创造者的唯一性,同样不是事实判断,而是我们又一次面临的价值选择。
信息来源:中国版权服务
本文首发于《中国版权》杂志2018年第2期,原文注释省略。我中心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