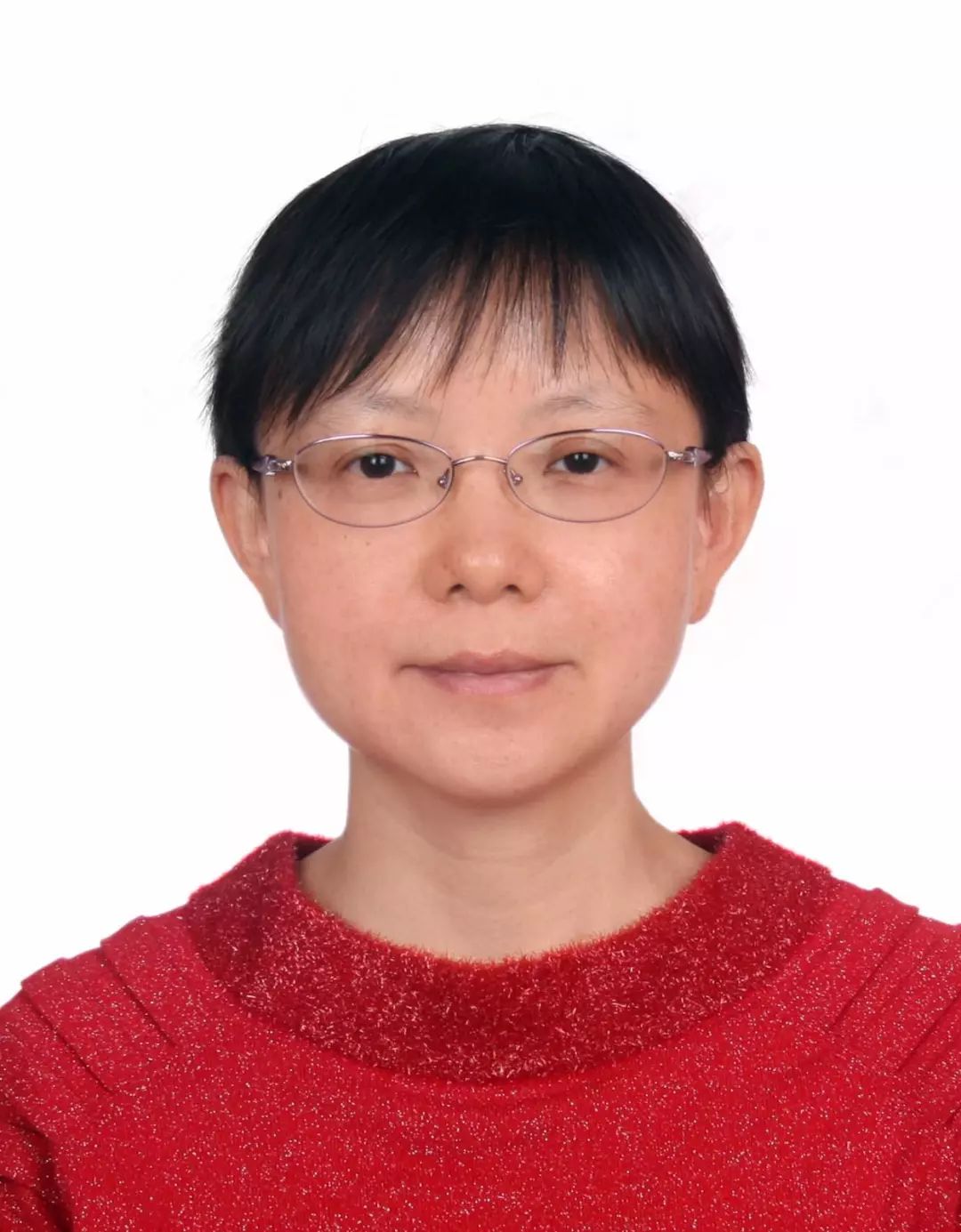
李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与邻接权教席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尤其偏重基础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专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论文《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化”》《“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为模型》。暇以诗文创作为娱,有志于“以美文抒法理”,曾发表《法题别裁》等系列知识产权随笔。
中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被视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被动立法到主动立法”。这种转变不是立法者的任意设想,而是社会现实变革的结果。这一现实基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社会形成了与著作权相关的独立诉求,产业实践与司法经验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规范方案。不仅立法要回应这种变化,知识产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应具有变革的自觉。在理论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实践与司法经验的不断丰富,学界应当改变过度倚重比较研究、直接搬运外国术语、各自炮制新概念的格局,更多地关注本土问题,在梳理本土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自洽的理论,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共识达成。在实践方面,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技术与商业模式更新的日趋频繁,应当告别立法中心主义,重视法律解释,不能事事仰仗“修法”,要善于通过合理解释在既有立法之下解决问题。知往以鉴今,秦瑞玠于1914年出版的《大清著作权律释义》(原题为《著作权律释义》,下文简称《释义》)【1】,对我国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的转型均具有启示意义,值得关注。
我国知识产权法学有关历史的研究不多,已有成果也是以制度史为主,学术史近乎空白。理论研究欲从“比较与移植”转向独立思考,不可忽略本土的学术历史资源。学术的演变,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轨迹而“进步”。事实上,《释义》中的一些观点在新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之后又重新成为探讨的话题。兹举两例:
1.著作权与民法的关系。《释义》在“著作权律之性质”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著作权为个人之私权。著作权律,为关于个人私权之规定。其性质为私法,为民法之特别法,亦即为民法法典以外之单行法……而著作权律,实为民法以外规定私权之单行特别法。”知识产权究竟是否为私权,学术界曾有争议,争议的平息主要是因为TRIPS协议开篇写明“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殊不知近代学者对此早有清楚的认识。
书中不仅阐明了著作权的私权属性,而且处处结合民法原理诠释条文。在解释“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时,作者把出资者和作者的关系分为四种,分别对应于民法上的“让渡契约”“请负契约”“雇佣契约”和“营利组合契约”。又如,《大清著作权律》第四十七条规定:“侵损著作权之案,如审明并非有心假冒,应将被告所已得之利,偿还原告,免其科罚。”作者用不当得利理论予以解释:“盖虽非不法行为,而究为不当利得,自不能免偿还之责任。”书中体现出作者在民法框架下研究著作权制度的理论自觉,而割裂知识产权与民法理论,仍是当下知识产权研究的缺陷之一。
2.著作权与出版管理的关系。在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于2010年修订之前,著作权与出版管理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修订之后,立法删除了“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表述,增加了“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的规定。质言之,区分了出版管理与著作权保护。《释义》对此已有明白的阐述:“著作者固纯为权利,而非有何等之义务,及负何等之责任,有与以奖励保护,而无所用其防制禁限,与警察法令之出版取缔法迥异。”
在绪论部分,作者区分了“解释论”和“立法论”,明确本书是解释论,旨在“疏通证明之,便于法律之实施而已”,而“至若依据学理,与各国法制比较研究,就立法论,为可否得失之评决,固非本编之范围所及也。”立法论与解释论的混杂,在今日知识产权研究乃至实践中,时有发生,本应以解释“疏通”之处,直接代以立法批评或修法建议。
在解释方法的运用方面,《释义》也颇值圈点,举隅如下:
1.对立法疏漏之处,作者在立法文义可容纳的范围内提出符合现实需求的解释可能。例如,《大清著作权律》在列举作品类型时未提及学术著作,作者认为,“而学术实为著作之大宗,与文艺、美术相鼎峙,断不容缺漏。是惟有于解释中补足之,而以条文所云文艺,解如文学之意义,始可。”
2.对立法表述不确之处,作者结合法理对表述的含义予以澄清。例如,《大清著作权律》把著作权登记称为“呈报义务”。作者指出,此处的“呈报义务”应解释为“呈报方法”。依据在于,“盖义务必须强制履行,违反者应受制裁。” 违反义务须承担责任,不登记著作权并不会导致责任的产生。因此,尽管立法采用了“呈报义务”的表述,《释义》认为,“以呈报方法或手续解之可也。” 又《大清著作权律》第五十四条规定,“本律施行前已发行之著作,业经有人翻印仿制,而当时并未指控为假冒者,自本律施行后,并经原著作者呈请注册,其翻印仿制之件,限以本律施行日起算三年内,仍准发行,过此即应禁止。” 从字面来看,“当时并未指控为假冒者”似乎是指事实上没有指控。但作者认为,“本条指控二字,实含广狭二义。狭义须有指控之事实,广义止谓得有指控之权利。”而后结合规范目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指出“其义属于不能,而非由于不为。”
3.在立法未明之处,作者结合民法原理和条文的整体关系做出合理的推导。例如,《大清著作权律》第四十一条规定,“因假冒而侵损他人著作权”的,科以罚金,并责令假冒者赔偿。而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则规定,违反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主要包括割裂改窜作品、割裂改窜及变匿作者署名、假托他人姓名发行作品、对教科书的习题擅作答词发行等行为)以及违反第三十九条者(引用作品不注明出处)仅科以罚金。从字面来看,这些行为似乎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但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理由有三:其一,“本律第三十四至三十七及三十九各条,同为假冒而侵损他人之著作权,是即民法上之不法行为……自应一律使负损害赔偿之责”;其二,仅仅科以罚金,责任过轻,“且区区十元、二十元以上之罚金,亦不足以示禁”;其三,“且视第四十七条非有心假冒者,犹须返还已得之利”,如果有意违反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以及第三十九条者不需要赔偿损失,“亦殊失平也”。这种考察法条之间的关系、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技巧,可资实务界借鉴。
资料总是随着时间不断更新,思想却未必。《释义》一书反映出的理论水平和解释技巧,今人未必皆能超越。欠缺体系化思维,不善于对法律概念做出具有规范意义的解释,仍是当下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的不足。如果忽视历史资源,我们会错失本应达到的起点高度。
注释
【1】秦瑞玠:《大清著作权律释义》,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本文首发于《中国版权》杂志2019年第3期。中国版权杂志微信公众号经授权转载,我中心经授权予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