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三月以来,我中心通过线上直播方式开展“君策讲堂”活动,先后推出“商标评审实务系列”、“商标审查、异议实务系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务系列”培训,近期,我们整理了讲堂嘉宾演讲稿件,并将陆续发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今天,推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何琼的演讲:商标权滥用的司法规制。本文经君策中心整理,何琼法官审定并授权,予以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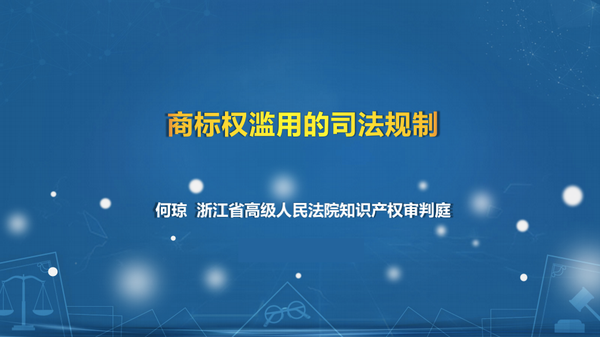
很高兴接受君策讲堂的邀请,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商标权滥用的司法规制。这个问题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司法中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大家都知道,近期出现了一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热门词汇,有的企业或者个人立即就对这些词汇申请注册,包括“火神山”“雷神山”等。对于这一情况,国知局反应非常迅速,马上出台了相关文件,并且在3月3日和5日分两批驳回了相关词汇的商标申请。3月26日,浙江省绍兴市市场监管局还对申请注册“李文亮”商标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这无疑能够更好地惩戒这种恶意注册行为。可见,虽然近几年一直在强调规制商标恶意注册,但从上述事件来看,商标恶意注册的现象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但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随着大家认识的深入和一些措施的跟进,这个现象也会慢慢得到遏制。今天的主题用了“商标权滥用”一词,因为商标恶意注册更多的是从行政机关前端进行的规制,从司法角度讲可能就不是很切题,所以我从商标权滥用的角度来设定了题目。
商标恶意注册跟商标权滥用,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问题。首先,商标恶意注册更多的是从权利取得的角度来讲的,商标权滥用则是从取得之后权利的行使过程中,或者是在维护所谓权利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滥用行为。第二,恶意注册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事前审查把关,商标权滥用则是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发生纠纷,通过司法渠道进行事后救济。第三,对这两种行为进行规制的主体分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前端把关往往更有效率,但司法也应当回应遏制商标恶意注册的现实需求,发挥司法的作用,所以司法在事后救济的领域也是应当有所作为的。
一、商标司法政策的演变
首先要讲一下从2008年开始商标司法政策的演变。我是2007年进入高院参加工作的,此后一直从事知识产权审判,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关于商标与其他知识产权尤其是字号权冲突的论文特别多。2008年,最高院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这个规定只有4条,但是对于原先的一些商标司法理念进行了澄清。该规定明确“注册商标侵害他人在先企业名称权、著作权、专利权的,法院应当受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及适用法律”。例如当事人有证据表明注册商标侵犯其在先著作权的,法院可以认定侵犯著作权,或者当事人有证据表明注册商标侵犯其在先企业名称的,法院可以认定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即根据具体的案由来确定。之前不少人认为商标一旦获得注册就享有了专用权,其他权利就无法对商标权造成冲击,但是上述规定就明确了商标即使取得注册,但如果实质上是侵害他人在先权益的,法院对于这类纠纷是可以审理的。但是,上述司法解释同时规定了“商标与商标之间的争议,法院不予受理”。从理论上说,注册商标之间的争议和其他在先权利与注册商标之间的争议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考虑到维持集中授权确权机制的需要以及相关规则标准统一的问题,所以在配置权力时把注册商标之间的争议交由行政机关处理,法院不再受理。我个人认为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而不是根据法理。这个规定在后面还会继续提到,因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或多或少还是会碰到虽然表面不是但实质上仍是注册商标之间争议的情况。虽然两个注册商标之间的争议法院不予受理,但是也存在例外,比如说如果权利商标属于驰名商标,根据驰名商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法院是可以受理的。还有就是超出核定使用范围,或者改变注册商标形态,将注册商标进行拆分或者组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注册商标已经不是商标注册证上的商标形态了,对于这种争议法院也是可以受理的。
2009年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意见》当中,最高院明确了权利冲突案件的审理原则,即诚实信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先权利。有工商登记等合法形式,但实质上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依法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因为字号与商标冲突是当时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特别进行了规定。企业名称权本身有工商登记的合法形式,但并不是有了合法的外衣就不会构成侵权。当时有一些典型的案例,还涉及到一些在境外比如香港等地注册的企业名称,使用这种企业名称同样也可能在境内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此外,《意见》还提到妥善处理注册商标实际使用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关系,使民事责任的承担有利于鼓励商标使用,激活商标资源,防止利用注册商标不正当地投机取巧。有一定商誉的注册商标在判赔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判赔额,因为商标的保护是要跟知名度、显著性相适应的,判赔的标准也同样要匹配。如果是没有经过实际使用或者注册三年后都没有使用的,这时的损害赔偿数额就比较低,可能只有合理维权费用。
2010年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公报案例,是最高法院(2008)民提字第36号“正野”案。这个案件现在看来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但在当时确实是规制商标权滥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对于我个人而言,也纠正了我当时的一些错误观念,所以印象很深。这个案例是在先字号诉在后商标,原告有一个在先使用的“正野”字号,被告在后注册了一个“正野”商标,法院认定商标使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且直接判决被告停止使用该商标。民事诉讼中不会对商标效力作出评判,但是可以从民事责任停止侵害的角度进行判决,所以实质上是否定了被告的注册商标,这一商标虽然没有被行政机关无效,但已经无法使用了,也就是一个死商标了。
跟这个案例相关的还有一个2010年度报告案例,是最高法院(2010)民提字第15号“王将”案。这个案件正好相反,是在先商标诉在后企业名称,我们刚才说在权利冲突领域有一个原则是保护在先权利,但是这个案件恰恰没有保护在先商标。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哪里?法院之所以没有认定被告的在后企业名称构成侵权,考虑到了以下几点理由:首先,该在先商标在被告字号登记的时候知名度并不高,且使用范围仅仅局限在哈尔滨;其次,被告是日本王将株式会社投资成立的,可能去过日本的朋友也看到过“王将”,在日本这是一家很早成立,知名度也比较高的公司,开了很多家连锁餐饮店,被告就是日本的“王将”当时想进入中国而注册的企业,所以被告作为日本王将株式会社投资的企业,使用“王将”字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从具体的使用形态来看,法院认为如果被告规范使用企业名称全称,是不会导致混淆误认的,所以没有认定企业名称全称的登记和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是对于突出使用“王将”字号的行为,法院是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的。所以这个案例是并不常见的在先商标没有得到保护的情况。所以就算是在先注册商标,但如果知名度非常低,并且被告注册及规范使用企业名称有一定合理性,也不导致混淆误认的话,也不一定得到保护。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是山东高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155号“张裕卡斯特酒庄”案,这个案件入选了2015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这是一个确认不侵权的案子,因为有自然人注册了“卡斯特”商标并发生了一些纠纷,张裕公司就对自己在酒庄等产品、服务上使用“张裕卡斯特”的行为合法性产生了疑惑,于是提起了确认不侵权之诉。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张裕公司使用“张裕卡斯特”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理由跟上一个案件相似,一是被告商标的知名度不高,二是“张裕卡斯特酒庄”这个名称的使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该酒庄是张裕跟法国卡斯特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一个酒庄,所以他们使用张裕和卡斯特来共同命名酒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正野”和“王将”两个案子,一个是在先字号诉在后商标,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一个是在先商标诉在后企业名称,法院认定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看起来似乎结论不同,背后的逻辑实际是一样的。因为在考虑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时候主要有两点,一是看被告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二是看客观上会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如果具备这两点就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之则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另外像山东“卡斯特”的案子,有时注册商标权人存在一些疑似商标滥用的情形,但又很难确切认定,那么通过弱化保护知名度低的商标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商标权滥用的效果。
2011年,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 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大发展大繁荣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属于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被诉侵权的在先商标使用人以此为由提出抗辩的,应当予以支持。这个规定指的是在民事诉讼中,被告如果以上面的三项理由作为不侵权抗辩,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这三项本来是商标的审查与核准章节里的条款,对于在商标授权确权阶段存在上述三种情形的,商标不应获得注册或者应当被撤销、无效,是没有争议的。但在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以这些理由作为抗辩,法院是否可以采信当时还存在一定争议,所以最高院在此明确了在商标授权确权中的这些理由,也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被告的不侵权抗辩事由。
最高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歌力思” 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最高法院2014年发布的一个指导案例,对于法院的在后判决是有一定拘束力的。在“歌力思”案中,原告为自然人,其在后注册的商标与被告女装品牌“歌力思”公司的在先字号和在先商标的文字部分完全一致。二审法院当时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最高院认为原告取得的商标权实质违法,不应当受到保护。这个案件引发的思考是,在被告以存在在先商标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法院如果认为在先注册商标可以构成抗辩理由,实际上就是对两个注册商标之间的纠纷作出了判断。这虽然在形式上不是两个注册商标之间的纠纷,但法院实质上处理了两个注册商标之间的争议,这是对于前面我所提到的法院不直接审理注册商标之间的纠纷这一限制的突破。当然,上述案件中这一情况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毕竟被告存在一个在先字号,即使被告没有在先注册商标,也可以用在先字号作为抗辩。
二、商标权滥用的主要行为类型
这一部分结合个案介绍一下商标权滥用的主要行为类型。
(一)利用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牟取不当利益
(2018)浙01民终4546号“确美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余杭法院一审、杭州中院二审的案件,是一起电商领域注册商标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典型案件。在电商领域,有些投诉人通过电商平台的“通知-删除”机制,利用不正当注册的商标进行投诉从而获利。本案被告李某在原告拜耳公司已经注册“Coppertone”“确美同”系列商标的情况下,将原告产品装潢中由原告享有在先著作权并在先投入商业使用的图形(如下图)申请注册商标,并于2016年被核准注册。




(原告在先创作并使用的作品)
在获得商标核准注册后,李某并未将上述商标用于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而是在淘宝平台对销售拜耳公司相关产品的网店发起大规模、持续性投诉,就涉案商标一共投诉了249次,涉及到121个商家。李某在涉案注册商标之外,还申请注册了113个商标,基于其中8个商标共进行2605次投诉,涉及1810个商家,其QQ自动留言中明目张胆地写着“付费撤诉,5万元起”。这种利用注册商标投诉网店经营者的行为,对电商领域的正常经营秩序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双11”等节庆日促销期间,很多商家可能会选择交钱给商标恶意注册人来息事宁人,继续经营,所以很多其实都没有进入到诉讼领域。但通过本案相关事实可以看到,商标恶意注册和滥用行为在现实中确实频频发生,这种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判赔70万元。
(二)抢注他人使用在先的未注册商标并牟取不当利益
未注册商标不属于知识产权专门法规定的权利,所以把它跟前面的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情况区分开来,作为滥用权利的另一种情况。当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未注册商标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保护,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虽然不能积极主动地主张权利,但是当他人发起诉讼时,可以作为有效的不侵权抗辩事由。这类情形其实在前几年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多了,2012年最高院的(2012)民申字第1475号“哈纳斯”案是一件比较典型的案件。该案中原告高某某诉被告哈纳斯公司侵害商标权,哈纳斯公司就是以其在先未注册商标来进行抗辩的,因为在原告注册涉案“哈纳斯”系列商标之前,哈纳斯公司已经在相关服务上使用该商标并且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法院最终也支持了哈纳斯公司的抗辩。
(三)将通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牟取不当利益
这类案件在电商领域也比较常见,我们去年进行电商平台知识产权责任调研时,平台就提到有些人把“破洞”“呼啦圈”等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然后进行大面积维权投诉。这里我想分享的典型案件是(2018)浙民终37号科顺诉共利案,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属于同一区域、同一领域的竞争者。前案中,共利公司曾以其注册的“CPU”商标权起诉科顺公司,但法院以“CPU”系建筑行业“浇筑型聚氨酯”的通用名称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是科顺公司在前案被诉以后,反过来要求共利公司承担其因恶意诉讼行为而导致的法律后果,法院不仅认定共利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而且判决支持的赔偿范围包括三部分:应诉费用、因行政投诉导致的货损及向第三人支付的违约赔偿,以及商标无效宣告费用,判赔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四)无使用意图大量囤积注册商标,牟取不正当利益
在2018年最高院再审改判的“优衣库”系列案件中,没有证据显示原告的涉案商标侵害了被告的在先权利或者权益,但原告注册商标共计两千六百多件,其中有一部分商标与他人在先知名商标高度近似。下面两个图左边是原告的注册商标,右边是优衣库的在轻型羽绒衣上面使用的标识,都是“UL”的,只是字体稍微有一些区别。


原告起诉优衣库使用“UL”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但原告不以使用为目的大量注册商标,并进行公开售卖,在本案中,原告也曾经向优衣库公司提出以800万元转让诉争商标。这批案子因为原告是以优衣库在全国的各家门店为被告进行起诉的,所以在全国各地法院都有相关诉讼,但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主要存在着4种裁判观点:
1.认定侵权成立,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这一观点是基于这两个“UL”标识本身基本无差别,或非常近似,所以认为侵权成立。
2.认定侵权成立,停止侵害但不赔偿损失。这是因为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实际使用行为,所以没有判决赔偿损失。
3.不构成混淆性近似,不侵权。在这种观点中,法院其实认为原告的行为具有不正当目的,不想保护原告,但又感觉认定原告恶意注册的依据不足,所以选择了一种比较保守的途径对原告不予保护。
4.原告注册及维权行为不正当,被告不侵权。这是相对来说最为激进、对商标滥用规制最为严格的一种观点,就是判定原告的注册和维权行为不正当,因为原告大量囤积商标且没有实际使用意图,却大规模发起诉讼以期牟取不当利益。
最高院再审判决认为,原告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意图高价转让于被告,在转让未果的情况下,又利用优衣库门店众多的特点,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在各地提起批量诉讼,滥用权利,违反诚信,故不予保护。所以,就裁判导向而言,对于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涉案商标存在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情况,但是却存在大量囤积商标的行为,法院倾向于不保护。但是由于在本案再审改判之时,原告的“UL”商标已经在全部商品类别上被宣告无效了,所以在涉案商标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无疑地说最高院对这种囤积的注册商标是不予保护的,但我个人认为司法趋势可能会慢慢往这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