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与邻接权教席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尤其偏重基础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专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论文《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化”》《“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为模型》。暇以诗文创作为娱,有志于“以美文抒法理”,曾发表《法题别裁》等系列知识产权随笔。
“金庸诉江南”案近日出了一审判决,案件的起因是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被移用到另一部作品中,虽然在时空上发生极大的转换,毕竟是让原著人物的故事继续下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续写。
金庸先生的随笔集《寻他千百度》中正好有一篇“书的‘续集’”,我们不妨看看原告站在文学立场而非官司立场上的续写观。文章的话头由一本伪托金庸之作的《天池怪侠》引起,此书用了天池怪侠、陈家洛等诸多《书剑恩仇录》中的人物名称,实为《书剑》的续作。接下来金先生举了很多旧小说续写的例子:《济公传》《七侠五义》《今古奇观》《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说唐》《西游记》《杨家将》等等。金先生提了一些颇值关注的看法和问题,兹原文摘录:1、“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2、“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写一部小说呢”?3、“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4、“既然《书剑》用的是旧小说体裁,尽管内容毫不足道,但出现续集倒也是合于传统的事,只是在封面上署了我的名字,那位作者似乎是过谦了”。
金先生认识到续写是一种文学传统,其实续写并不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传统,也不只小说可以被续写,带有叙事性的诗歌也不乏续写的例子。仅英国剧作家兼诗人马洛的诗作《牧羊人恋歌》,就有大量的续作,包括巴恩菲尔德的《深情的牧羊人》、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雷利的《美女答牧羊人》、布雷顿的《多情的牧羊人》、多恩的《诱饵》、赫里克的《致菲利斯,爱他并和他同居》、沃尔顿的《娴熟的垂钓者》、刘易斯的《歌两首》和纳什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统治下的爱》等。《牧羊人恋歌》是以一位牧羊人向恋人求爱的口吻写成的,表达了对乡村田园生活和理想爱情的追求。这些续写作品或是制造了一个恋人另有所爱的结局(《深情的牧羊人》)、或是以恋人的口吻回应牧羊人(《美女答牧羊人》)、或是改造成针砭时弊的讽刺诗(《共和党或民主党统治下的爱》)。
在美学理论中,续写属于互文的一种形式。“互文性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或惯例的一种共同累积的参与等。” 互文的目的是通过重复原著的部分表达,建立文本间的链接关系,唤起读者对原著的联想,从而引起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这种效果是完全孤立(绝对原创)的文本无法具有的。引用、戏仿、续写的美学依据皆在于此。为了达到唤起阅读记忆的效果,续写者选择的作品大多是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有少数例外)。而且这些作品的经典程度,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一种高度的典型性,成为特定文化中的符码,甚至具有性格理念的属性,例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黄蓉的娇俏机敏,也容易引发后来者在此性格理念之上再塑新表达的冲动。有时,反原著之道的续写还构成一种文学批判。“总的来讲,互文关系可以分为两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和否定的互文关系。前者指运用前文本的情节敷设自己的篇章、采用原作主题或直接引用原作诗句等;后者指在人物塑造方面对原作人物进行改造、对前文本内容进行戏仿、批驳和改编等。” 因此,续写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有其美学根由。续写具有原创所无法达到的某些美学效果。
对于仅仅利用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的行为,我国知识产权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不侵犯著作权,这是合乎法理的。由人名而建构的续作与原作的关系(互文关系),是靠读者的联想完成的,续作中并未复制原作的表达。争议主要在于“利用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复杂,涉及到不同的价值权衡。主张不正当竞争的论者看重的因素主要有:被告借用了原告作品的声誉;原告自己的续写利益可能受损;原告的情感因素等。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保护的依据是不正当竞争,就意味着在逻辑上存在“正当利用”的可能性。如果只要是利用就不正当,无异于把“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当作了绝对权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作品的传播通常能产生利益,如果“续作产生利益”本身就可以论证非法性,也基本上否定了正当利用的可能。因此,既然否定了人物名称和人物关系的著作权保护,就应当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利用,无论是否获得商业利益。有文艺评论者认为,“中外文坛上不乏靠引用、续写、模仿、奉和或反驳他人作品而使自己作品引人注目乃至使自己声名显赫的例子,这恰恰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的魅力。” 客观上借用了原作的声誉,也并不当然非法。
法律对作者之间的关系调整应当尊重创作的现实与传统。著作权法大体上是根据现代作品观建构的,偏重作者对文本的控制(例如保护作品完整权)。后现代作品观则更注重文本潜藏的可能性,续写在本质上是对文本可能性的继续挖掘。虽然法学不能等同于美学,作者利益依然是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但任何创作手法——即便是边缘性的,都应当获得存身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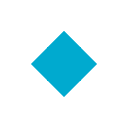
续写者与原作者的利益冲突是必然存在的,裁判者只有尽力全面地发现所涉的重大利益,才有可能做出最合理的决断。续写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当然不可一概而论,需个案考量。本文希望提示的是:作为一类文学存在,追求互文效果的作品,在法律上应有被容许的空间。戏仿已经被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确立为合理使用,即为一例。在评判续写的合法性时,“文化多样性”应作为一个重要价值因素予以考虑,续写者征得原作者许可的难度也不应被忽视。司法裁判宜在商业利益和文化发展之间求得平衡。
相关链接,点击阅读:
信息来源:中国版权杂志
本文首发于《中国版权》杂志2018年第5期,原文注释省略。我中心经授权转载。